|
抖音充值 1971年,我还不到17岁,懵懵懂懂地跟着同学们一起到舒兰县的一个生产队插队落户,从此开始了六年的知青生活。 初到农村,队里给我们准备了一些柴火烧饭,但是量不足,只能用几天,要想吃饭就得自己上山去打柴。打柴在秋天。那时,山上的柴草都长高了,田里的活也不多,队里会专门腾出十来天的时间,让大家上山去打柴草,以备下一年所需。平时,生产队安排出工很紧,没有时间上山打柴草,所以趁着这段时间,我们都是早出晚归,巴不得一天当两天用。 平时,知青们和社员一样,每天都要出工,一天差不多能挣五、六个工分。综合下来,累死累活干一天差不多是四、五角钱。不出工是不行的,会被贫下中农认为你不积极,影响以后的前途……所以,知青们虽然并不是那么看重那点工分,但还是要天天出工的。只有打柴草的这段时间才不用出工,我们那些知青们兴奋异常,差不多把这十来天砍柴日当作放长假,东溜西逛的,早把打柴草的事丢到脑后。虽然多少也去弄些回来,但不用说存够一年烧的,就连一个月都不够烧。十几天很快就过去了,农民房前屋后堆着一大垛一大垛的柴草,而我们知青小院里只是一小堆,看着都令人汗颜。 不出所料,柴草很快就要烧完了。虽然大队有规定,过了统一打柴草的时间就不允许上山砍柴了,可没柴烧也不行。所以知青是特例,特例物办,什么时候都能去。因为附近的柴草都被农民砍光了,我们只能上更高更远的山,要费更多的劲。这下,大家傻了眼,早知今日,何必当初呢?一个个叫苦不迭。 于是,只要是能烧的,我们就会想尽办法去弄来,就连散了的尿桶也当柴烧了。最后实在没得烧了,便半夜三更去偷农民的柴草。农民心知肚明,但对知青还是比较宽容的,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不去追究。 但事情总有料想不到的时候,一连下了几天雨,半夜又起风,把厨房的屋顶掀去一大片,雨水把放在厨房里当柴火的稻草都浇个湿透。早上起来,我们不由暗暗叫苦,这顿饭该怎么做?大白天的,众目睽睽之下,想去偷柴草是没戏了,只好把那些稻草稍干点儿的,倒上油灯里的煤油点着,勉强煮起饭来。但那些稻草实在大湿了,煤油烧完后,稻草只冒烟。再添煤油,但也只是烧一会儿的火,很快又是一屋子的烟。折腾来折腾去,煤油也没有了,而锅里的饭还半生不熟。没辙了,只好将就着硬是吞下肚。 二队的知青住的是一个老祠堂,大厅左右隔了两间让知青住,中间-大片就存放些队里一时没用的东西,比如打谷机、大油筒(里面有剩余的煤油底),还有一些盖房子剩余的木料。因为平时这些东西用不上,队里也就很少来看看东西究竟少了没有。也因为只要大门一关,里面干什么谁也不知道,知青们居然打起了这些东西的主意。 开始时,知青们只是偷偷拿点,生火时把柴油浇在木柴上。到后来木柴烧完了,眼看饭要煮不成了,不知是谁突然出个主意,拿块砖头浸到柴油里,砖头吸饱柴油,放到炉上,再拿张纸引上火,果然腾腾地烧起来。一看效果不错,又添了几块吸饱柴油的砖头进去,一顿饭就煮好了。 有了这些柴油,知青们可是过了一段好日子,砖头能煮饭的事也成了一个秘而不宣的事。好景不长,本来大油桶里的柴油就不多,如此一日三餐,终于告罄。但好在还有一堆木料,也可以派上用场,都是煮饭的好材料。虽然大家也感到把这些木料当柴烧有点儿可惜,但肚子的事要紧,也就顾不上什么大材小用了。 一段时间以后,那些木料日渐减少,终于被队里发现了。队长问东四哪里去了,大家都装聋作哑,推说不知道。队长没辄,只好作罢,但以后,就再也没把能烧的东西放在祠堂里了。 岁月如梭,转眼半个世纪过去了。知青们如今基本都已年过花甲,容颜已退,脸上写满了沧桑的皱纹,那千般风情已白了如墨青丝。曾经的那种生活,那种经历,早已铭刻在心,溶于血脉,成为今生今世永不褪色的记忆。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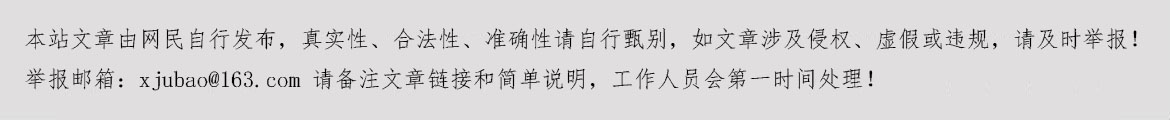
|